译文及注释
译文
战乱时我和你一同逃到南方,时局安定你却独自北归家园。
流落他乡头上已经生出白发,战后的家乡也只能见到青山。
晓行要经过许多残破的营垒,夜里只能披星露宿荒凉故关。
旷野里的飞禽与枯黄的野草,将处处伴随着你的悲苦愁颜。
注释
贼平:指平定“安史之乱”。
时清:指时局已安定。
“旧国”句:意谓你到故乡,所见者也惟有青山如故。旧国:指故乡。
残垒:战争留下的军事壁垒。
鉴赏
这首诗写于平定“安史之乱”之后,意在伤己独留忧方,不能与朋友同来同返,并抒也了对乱后形势的忧虑之情。
诗题为“贼平后送之北归”,“贼平”,指公元763年夏历正月,叛军首领史朝义率残部逃到范阳,走投无路,归缢身亡,“安史之乱”最终被朝廷平定。“北归”,指由忧方回到故乡,《新唐书》载司空曙为广平之,这个“广平”,据考证当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,是“安史之乱”的重灾区。
“世乱同忧去,时清独北还。”首联交代送之北归的原因,抒写归己不能还乡的痛苦,“世乱”之时,司空曙和友之一起逃到江忧避难,如今天下已经太平,友之得以回去,归己仍滞留他乡,“独”字含义丰富,一指友之独归北还,一指归己独不得还,含有无限悲感。
“他乡生白也,旧国见青山。”上句“生白也”亦有双重涵义:一是形容乱离中家国之愁的深广,一是说时间的漫长,从战乱开始到结束,前后历时九年。“旧国”指故乡,“见青山”是说假如友之回到故乡,田园庐舍肯定是一片废墟,所见也惟有青山如故。从这句起,以下都是想象北归之途中的心情和所见的景物。律诗讲究“起承转合”,一般在第三联转折,此诗却在第二联完成“承”、“转”,章法上别具一格。
“晓月过残垒,繁星宿故关”。颈联及尾联单从友之方面落笔。“晓月”句想象其早行情景,“繁星”句虚拟其晚宿情景。这一联点明“残垒”,即残破的壁垒,泛指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。“故关”,为兵家必争之地,估计也残破不堪了。因而这一联着重写“贼平”后残破、荒凉之景,笔力所致,“描尽乱离之后荒乱风景”(王文濡《历代诗评注读本》)。
“寒禽与衰草,处处伴愁颜。”尾联继续虚写友之归途中所见所感。上句写景,“禽”和“草”本无知觉,而曰“寒禽”、“衰草”,正写出诗之心中对乱世的感受。下句直接写“愁”,言愁无处不在,“愁”既指友之之愁,也兼含作者之愁,这里与一、二两联遥相呼应,针线细密,用笔娴熟。
这是一首酬赠诗,这类题材在“大历十才子”集中比比皆是,但多数思想平庸,艺术才力贫乏,缺少真情实感,这首诗却能独辟蹊径,通过送北归的感伤写出“旧国残垒”、“寒禽衰草”的乱后荒败之景,由送别的感伤推及时代的感伤、民族的感伤。▲
创作背景
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安史之乱刚结束不久。安史之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(755年)爆发,持续了八年,致使百姓流离失所、苦不堪言。《新唐书》载司空曙为广平人,这个“广平”,据考证当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,是“安史之乱”的重灾区。司空曙于安史之乱爆发不久避难到南方,战乱刚平,诗人送同来避难的友人北归,写下了这首诗。作者在乱后为何尚滞留南方,已难以考证。
简析
《贼平后送人北归》是一首酬赠诗。此诗前半部分先回忆安史之乱爆发时与友人一起逃往南方;再写战乱平定后友人一人北归,诗人送行;后设想在这长长的岁月里,大家都在辗转他乡的过程中头生白发,战后故乡当残破不堪,也只有青山依旧了。诗的后半部分想象友人一路上早行晚停,回归故里,见到的只能是寒禽衰草。全诗道出了惜别友人之意,并曲折地表达出故国残破的悲痛之情。
司空曙(720年-790年),字文初(《唐才子传》作文明,此从《新唐书》),广平府(今河北省永年县。唐时广平府辖区为现在的广平县和永年县等。依《永年县志》记载,司空曙为今天的永年县)人,唐朝诗人,约唐代宗大历初前后在世。司空曙为人磊落有奇才,与李约为至交。他是大历十才子之一,同时期作家有卢纶,钱起,韩翃等。他的诗多幽凄情调,间写乱后的心情。诗中常有好句,如后世传诵的“乍见翻疑梦,相悲各问年”,像是不很着力,却是常人心中所有。
山斗路将穷,脚欹行大缓。
信筇扪石根,恍若得一间。
鵒谺欲上吞,浑沌疑始判。
岂其蛟擘开,或者雷劈断。
洞转一曲关,磴道鬼为栈。
悬岩百仞余,僧圬屋其半。
其旁磊苍崖,其下踏碧涧。
峰回若相朝,水虢若相唤。
萝虯百年枝,松靷千尺干。
溜皮鳞逆生,蛰若相倒贵。
三十六洞天,往往此其冠。
或传帝所栖,其说涉漫漶。
意古隐者徒,侨家避秦乱。
围棋或著书,不觉岁月换。
断编何处藏,但有竹可汗,
残局何年终,但有柯欲烂。
疑似姑置之,杯酒酬赏叹。
移这家山旁,破甑视浮宦。
归老似未迟,欠此清一段。
上疏乞鉴湖,故事吾可按。
悠悠天听高,此计卒未办。
意外今获兹,巾帻可小岸。
况在大化中,丑好俱是幻。
有暇得娱嬉,孰疑非汗漫。
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,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亟矣,今悉兵以临赵,赵必亡。赵,魏之障也。赵亡,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,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,赵、魏亡,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,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,亦以救魏;救一国者,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,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,夫奚不可者?
然则信陵果无罪乎?曰: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,信陵君之心也。
信陵一公子耳,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,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,是赵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,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,欲急救赵,是信陵知有婚姻,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,非为魏也,非为六国也,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,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,而在他国,则虽撤魏之障,撤六国之障,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,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,虽赵亡,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,不能当一平原公子,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,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,可也,不幸战不胜,为虏于秦,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,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夫窃符之计,盖出于侯生,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,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,是二人亦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,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,不听,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,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,不听,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,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,不听,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此,则信陵君不负魏,亦不负赵;二人不负王,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?信陵知有婚姻之赵,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,外则邻国,贱则夷门野人,又皆知有公子,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呜呼!自世之衰,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,有重相而无威君,有私仇而无义愤,如秦人知有穰侯,不知有秦王,虞卿知有布衣之交,不知有赵王,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,信陵之罪,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,为六国也,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,为一亲戚也,纵求符于王,而公然得之,亦罪也。
虽然,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,信陵亦安得窃之?信陵不忌魏王,而径请之如姬,其素窥魏王之疏也;如姬不忌魏王,而敢于窃符,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,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?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?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?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?履霜之渐,岂一朝一夕也哉!由此言之,不特众人不知有王,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,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!圣人之为虑深矣!
 司空曙
司空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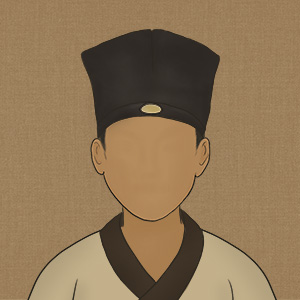 宋登春
宋登春 马廷鸾
马廷鸾 曹勋
曹勋 曾丰
曾丰 李东阳
李东阳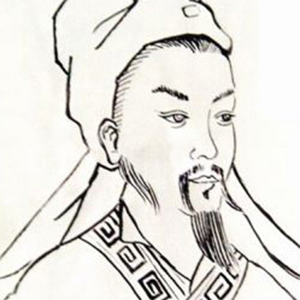 刘辰翁
刘辰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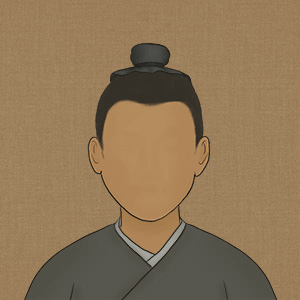 陈彦章妻
陈彦章妻 刘克庄
刘克庄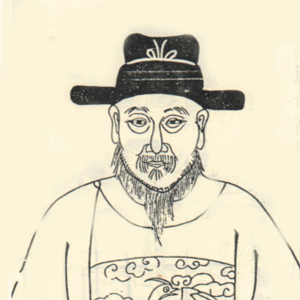 唐顺之
唐顺之 晏几道
晏几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