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高高的宾舍面对着荒芜的道路,清澈的流水连接着长长的小路。
在这髙岸上有位思绪飞扬的人,他怀着往昔的深情厚谊盼望着远游的朋友早日归来。
水塘边的草丛中野花已绽开了红英,林中的花木还点缀着一些已经泛白的春花(点名季节,在春夏之交)。
回望日落的地方就是繁华的都城,为什么在这暮春季节、都城旁边摆设的都是离别的筵席?
注释
水曹:官名。
高馆:高大的馆舍。
荒途:荒芜的道路。
长陌:长路。
重城:指宫城、都城。
鉴赏
六朝谢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,世称“永明体”,代表谢人则是谢朓,他上承晋宋,下开唐风,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。明人钟惺称二谢谢均多排语,“然康乐排得可厌,却不失为古谢。玄晖排得不可厌,业已浸淫近体”(《古谢客》)。明人许学夷也说:“元嘉体虽尽入俳偶,语虽尽入雕刻,其声韵犹古”,至沈、谢则“声渐入律,语渐绮靡,而古声渐亡矣”(《谢源辩体》)。一古一近,判然有别。小谢的“新变”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谢中也可窥其端客。
理解这首谢,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:题面上是“还远馆”,而开头第一句即是“高馆临荒途”,那末两个“馆”字所指是一,抑或是二?若此“高馆”即题中与“远馆”,则所写为悬想与词;若否,则是实写送别与地的景色。揣摩全谢,细绎词意,毋宁作后一解为是。
首联分别从高、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:荒郊野途,高馆孤峙,清流映带,长路迢递。馆,即客舍,安顿宾客的馆舍,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,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,谢人将与他举袂相别。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客。此处着一“带”字尤为传神: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,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。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客与情。“流思”,即思客飘忽不定,流荡无住与意;“怀旧望客客”则为“流思人”与同位语。“怀旧”,怀念旧邦或亲故与意;“望客客”,渴望客去与人,是为偏正结构,非动宾结构。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,此行所去,只是远馆,而非故乡,故而客中作客,无慰“怀旧望客”与情,只能更增羁旅情怀。但是谢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,而是重又转回写景。谢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,那池塘春草、花树相间、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。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,人不应该离别,而应该流连忘返,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,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。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,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。送君千里,终须一别,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,尾联重又客结到送别与意。“日暮有重城”,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,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客。天色将晚,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,故主客双方只得在“何由尽离席”的感慨中分道扬镳,谢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。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,结句将惜别与情发挥得非常充分。
离别是古谢中一个陈旧的主题。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谢,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“新变”来呢?最突出的一点是谢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、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。汉魏古谢多胸臆语,直抒所感,古朴质实,情语多于景语,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。而到了谢朓,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,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与中,二者不是游离与物,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,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,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、正面的表述。即以此谢而论,谢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,对别离与情几乎未作铺陈,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,情客的熏染,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。这就是后人所说的“风调”、“神韵”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小谢的谢成为唐谢的先声。试看王维的《客嵩山作》:“晴川带长薄,车马去闲闲。流水如有意,暮禽相与还。荒城临古渡,落日满秋山。迢递嵩高下,客来且闭关。”右丞此谢就是正从小谢谢中有所借鉴的。谢灵运也模山范水,但精雕细刻,失与板重,刻意写形,而乏情韵。玄晖则刊落繁缛,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。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谢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。唐谢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,情韵流动的意境,风神摇曳的格调,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。
其次,在谢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。自沈约倡“声律说”以来,谢人排比声韵,约句准篇,成为一时的风气,标志了五言古谢向近体律谢的过渡,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。严羽说:“谢朓与谢,已有全篇似唐人者。”(《沧浪谢话》)除风格而外,格律与新也是其一个方面。即以此谢论,除去押入声韵与外,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谢。首联对偶工切,但平仄不协,第二联不对,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。这在律谢中称为“偷春格”,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,恰如花儿偷得春光,先春而开。▲
谢朓(464~499年),字玄晖。汉族,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县)人。南朝齐时著名的山水诗人,出身世家大族。谢朓与谢灵运同族,世称“小谢”。初任竟陵王萧子良功曹、文学,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。后官宣城太守,终尚书吏部郎,又称谢宣城、谢吏部。东昏侯永元初,遭始安王萧遥光诬陷,下狱死。曾与沈约等共创“永明体”。今存诗二百余首,多描写自然景物,间亦直抒怀抱,诗风清新秀丽,圆美流转,善于发端,时有佳句;又平仄协调,对偶工整,开启唐代律绝之先河。
商君者,卫之诸庶孽公子也,名鞅,姓公孙氏,其祖本姬姓也。鞅少好刑名之学,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。公叔痤知其贤,未及进。会痤病,魏惠王亲往问病,曰:“公叔病有如不可讳,将奈社稷何?”公叔曰:“痤之中庶子公孙鞅,年虽少,有奇才,愿王举国而听之。”王嘿然。王且去,痤屏人言曰:“王即不听用鞅,必杀之,无令出境。”王许诺而去。公叔痤召鞅谢曰:“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,我言若,王色不许我。我方先君后臣,因谓王即弗用鞅,当杀之。王许我。汝可疾去矣,且见禽。”鞅曰:“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,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?”卒不去。惠王既去,而谓左右曰:“公叔病甚,悲乎,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,岂不悖哉!”
公叔既死,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,将修缪公之业,东复侵地,乃遂西入秦,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。孝公既见卫鞅,语事良久,孝公时时睡,弗听。罢而孝公怒景监曰:“子之客妄人耳,安足用邪!”景监以让卫鞅。卫鞅曰:“吾说公以帝道,其志不开悟矣。”后五日,复求见鞅。鞅复见孝公,益愈,然而未中旨。罢而孝公复让景监,景监亦让鞅。鞅曰:“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。请复见鞅。”鞅复见孝公,孝公善之而未用也。罢而去。孝公谓景监曰:“汝客善,可与语矣。”鞅曰:“吾说公以霸道,其意欲用之矣。诚复见我,我知之矣。”
卫鞅复见孝公。公与语,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景监曰:“子何以中吾君?吾君之欢甚也。”鞅曰:“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,而君曰:‘久远,吾不能待。且贤君者,各及其身显名天下,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?’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,君大说之耳。然亦难以比德于殷、周矣。”
孝公既用卫鞅,鞅欲变法,恐天下议己。卫鞅曰:“疑行无名,疑事无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,固见非於世;有独知之虑者,必见敖於民。愚者闇於成事,知者见於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於俗,成大功者不谋於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甘龙曰:“不然。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,不劳而成功;缘法而治者,吏习而民安之。”卫鞅曰:“龙之所言,世俗之言也。常人安於故俗,学者溺於所闻。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,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伯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,愚者制焉;贤者更礼,不肖者拘焉。”杜挚曰:“利不百,不变法;功不十,不易器。法古无过,循礼无邪。”卫鞅曰:“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法古。故汤武不循古而王,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,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以卫鞅为左庶长,卒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,而相牧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,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,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,倍其赋。有军功者,各以率受上爵;为私斗者,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僇力本业,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,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,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,各以差次名田宅,臣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令既具,未布,恐民之不信,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,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,莫敢徙。复曰“能徙者予五十金”。有一人徙之,辄予五十金,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令行於民期年,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於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: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。”将法太子。太子,君嗣也,不可施刑,刑其傅公子虔,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,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,秦民大说,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。民勇於公战,怯於私斗,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,卫鞅曰“此皆乱化之民也”,尽迁之於边城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於是以鞅为大良造。将兵围魏安邑,降之。居三年,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,秦自雍徙都之。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而集小乡邑聚为县,置令、丞,凡三十一县。为田开阡陌封疆,而赋税平。平斗桶权衡丈尺。行之四年,公子虔复犯约,劓之。居五年,秦人富强,天子致胙於孝公,诸侯毕贺。
其明年,齐败魏兵於马陵,虏其太子申,杀将军庞涓。其明年,卫鞅说孝公曰:“秦之与魏,譬若人之有腹心疾,非魏并秦,秦即并魏。何者?魏居领阨之西,都安邑,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。利则西侵秦,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,国赖以盛。而魏往年大破於齐,诸侯畔之,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支秦,必东徙。东徙,秦据河山之固,东乡以制诸侯,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孝公以为然,使卫鞅将而伐魏。魏使公子昂将而击之。军既相距,卫鞅遗魏将公子昂书曰:“吾始与公子驩,今俱为两国将,不忍相攻,可与公子面相见,盟,乐饮而罢兵,以安秦魏。”魏公子昂以为然。会盟已,饮,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昂,因攻其军,尽破之以归秦。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,国内空,日以削,恐,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,徙都大梁。魏惠王曰: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卫鞅既破魏还,秦封之於、商十五邑,号为商君。
商君相秦十年,宗室贵戚多怨望者。赵良见商君。商君曰:“鞅之得见也,从孟兰皋,今鞅请得交,可乎?”赵良曰:“仆弗敢愿也。孔丘有言曰:‘推贤而戴者进,聚不肖而王者退。’仆不肖,故不敢受命。仆闻之曰:‘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,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。’仆听君之义,则恐仆贪位贪名也。故不敢闻命。”商君曰:“子不说吾治秦与?”赵良曰:“反听之谓聪,内视之谓明,自胜之谓强。虞舜有言曰:‘自卑也尚矣。’君不若道虞舜之道,无为问仆矣。”商君曰:“始秦戎翟之教,父子无别,同室而居。今我更制其教,而为其男女之别,大筑冀阙,营如鲁卫矣。子观我治秦也,孰与五羖大夫贤?”赵良曰:“千羊之皮,不如一狐之掖;千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。武王谔谔以昌,殷纣墨墨以亡。君若不非武王乎,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,可乎?”商君曰:“语有之矣,貌言华也,至言实也,苦言药也,甘言疾也。夫子果肯终日正言,鞅之药也。鞅将事子,子又何辞焉!”赵良曰:“夫五羖大夫,荆之鄙人也。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,行而无资,自粥於秦客,被褐食牛。期年,缪公知之,举之牛口之下,而加之百姓之上,秦国莫敢望焉。相秦六七年,而东伐郑,三置晋国之君,一救荆国之祸。发教封内,而巴人致贡;施德诸侯,而八戎来服。由余闻之,款关请见。五羖大夫之相秦也,劳不坐乘,暑不张盖,行於国中,不从车乘,不操干戈,功名藏於府库,德行施於后世。五羖大夫死,秦国男女流涕,童子不歌谣,舂者不相杵。此五羖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见秦王也,因嬖人景监以为主,非所以为名也。相秦不以百姓为事,而大筑冀阙,非所以为功也。刑黥太子之师傅,残伤民以骏刑,是积怨畜祸也。教之化民也深於命,民之效上也捷於令。今君又左建外易,非所以为教也。君又南面而称寡人,日绳秦之贵公子。诗曰:‘相鼠有体,人而无礼,人而无礼,何不遄死。’以诗观之,非所以为寿也。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,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。诗曰:‘得人者兴,失人者崩。’此数事者,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,后车十数,从车载甲,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,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。此一物不具,君固不出。书曰:‘恃德者昌,恃力者亡。’君之危若朝露,尚将欲延年益寿乎?则何不归十五都,灌园於鄙,劝秦王显岩穴之士,养老存孤,敬父兄,序有功,尊有德,可以少安。君尚将贪商於之富,宠秦国之教,畜百姓之怨,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,秦国之所以收君者,岂其微哉?亡可翘足而待。”商君弗从。
后五月而秦孝公卒,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,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,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,曰:“商君之法,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叹曰:“嗟乎,为法之敝一至此哉!”去之魏。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,弗受。商君欲之他国。魏人曰:“商君,秦之贼。秦彊而贼入魏,弗归,不可。”遂内秦。商君既复入秦,走商邑,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。秦发兵攻商君,杀之於郑黾池。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,曰:“莫如商鞅反者!”遂灭商君之家。
太史公曰:商君,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,挟持浮说,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,及得用,刑公子虔,欺魏将昂,不师赵良之言,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,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於秦,有以也夫!
 谢朓
谢朓 陈著
陈著 司马迁
司马迁 赵蕃
赵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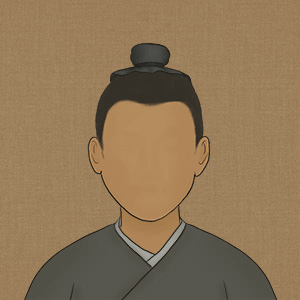 姬翼
姬翼 夏完淳
夏完淳 丰坊
丰坊 王庭珪
王庭珪 佚名
佚名 项安世
项安世 薛嵎
薛嵎